记事作文《路口》关于姐妹之间的故事 童年往事作文
柳下笙歌庭院,花间姊妹秋千。记得春楼当日事,写向红窗夜月前。凭谁寄小莲。——题记
一大一小的两个身影藏匿在一片墨绿的叶子中,沿着墙边蹑手蹑脚地一路挪动,密密的叶子像一池浮萍被分拨成两路。我领着妹妹小心蜷在这“路口”,来干这“见不得人的勾当”。

我用手攥紧茎,左右摇晃着来松动泥土,不一会半个萝卜就“呼之欲出”了。
“有人来了!”妹妹喊了一声,却不敢使劲。我一惊,把那萝卜一抛,拉起她的手咻地站起身,装作来这田路间散散步。
许是因为有了经验,这一次她格外地干脆利落,瞄准一株就下手,一番“折磨”之后,一株雪白白水灵灵的大萝卜带着沾泥的萝卜须冲我得意一笑。我拉了她的手出田回到路上,并让她抖干净裤管上的泥巴。她低头看了一眼,不知为何傻傻地笑了起来,笑得肆意张狂,全然忘却了我俩的小偷身份,为一株萝卜欣喜,真是丢了我们这职业的脸。
她的笑声惊起了一片白鹭,扑棱着翅膀在水田间四窜。芦苇也被这笑声感染,飘飘然同春天的柳絮一般轻盈,惹得我心痒。跑到这条田路上,我牵着妹妹的手,妹妹牵着胖白萝卜的手,一起沐浴芦苇的洗礼。明明是黄昏,晚霞的橙光悄悄涂抹着田间小路,却因为这芦苇微微的舞动,显出了几分清晨的寒光。
我与妹妹无数次地奔跑在这条路上,偷萝卜的激动,看芦花的恬淡,放风筝的喜悦……路把我和妹妹紧紧连在一起,却也让我们慢慢地、慢慢地分离。她开始跟不上我的脚步,我笑着打趣你说怎么一年不如一年,她气喘吁吁地弯着腰休息,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疑惑着呢,妹妹。为何你长大了,我们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了?水稻被插秧然后收割,毛豆被播种到摘获,岁岁又年年,一个我不情愿面对的现实正披露在我眼前:是我长大了。
后知后觉,原来她已不再复制我的脚步,渐渐从我走过路上渐渐去探寻自己的路,然后偏离轨道。
假装不经意地和她提及我这一种感觉,她低下头沉默了一会,抬起头来笑着说:“反正你永远永远是我的好姐姐呀。”我一怔。
在这个路口,我无路可退,是你把我针对。
- 热门课程
- 热门资讯
- 热门资料
- 热门福利
-
 黄河小班课人数多吗?教学效果怎么样?黄河小班课之前就有家长和学生想要了解过,今天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小编就来好好给大家解答一下关于黄河小班课的一些内容,让大家能够更加方便地做出选择。 一、黄河小班课人数多吗? 黄河小班课的人数控制得挺讲究,既不是那种三五个人的微型小组,也不会像其他学校那样挤着四五十个人,一个班大概在6到15人
黄河小班课人数多吗?教学效果怎么样?黄河小班课之前就有家长和学生想要了解过,今天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小编就来好好给大家解答一下关于黄河小班课的一些内容,让大家能够更加方便地做出选择。 一、黄河小班课人数多吗? 黄河小班课的人数控制得挺讲究,既不是那种三五个人的微型小组,也不会像其他学校那样挤着四五十个人,一个班大概在6到15人 -
 “白驹过隙”怎么读?到底有什么含义?“白驹过隙” 是形容时光的经典表达,可你真能笃定 “驹” 字读 “jū” 而非 “jú”?而且 “白驹” 为何是 “白色的小马”,“过隙” 又特指什么缝隙? 一、“白驹过隙”怎么读? “白驹过隙”的正确读音是bái jū guò xì,“白驹”指白色的骏马,常被引申为太阳的光芒或飞速流逝的时
“白驹过隙”怎么读?到底有什么含义?“白驹过隙” 是形容时光的经典表达,可你真能笃定 “驹” 字读 “jū” 而非 “jú”?而且 “白驹” 为何是 “白色的小马”,“过隙” 又特指什么缝隙? 一、“白驹过隙”怎么读? “白驹过隙”的正确读音是bái jū guò xì,“白驹”指白色的骏马,常被引申为太阳的光芒或飞速流逝的时 -
 博大单招在文化课提升方面优势如何?补习效果好吗?单招相信第一次接触的家长和同学们有很多问题都不了解,很多家长为了让孩子更好地学习就去选择一个合适的单招补习,那么博大单招在这方面的优势到底怎么样?能不能帮助孩子更好地提升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好好了解一下。 一、博大单招在文化课提升方面优势如何? 博大单招在文化课提升这方面那真的是研究得透透的
博大单招在文化课提升方面优势如何?补习效果好吗?单招相信第一次接触的家长和同学们有很多问题都不了解,很多家长为了让孩子更好地学习就去选择一个合适的单招补习,那么博大单招在这方面的优势到底怎么样?能不能帮助孩子更好地提升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好好了解一下。 一、博大单招在文化课提升方面优势如何? 博大单招在文化课提升这方面那真的是研究得透透的 -
 “琨玉秋霜”怎么读?到底有什么含义?“琨玉秋霜” 中的“玉” 和 “秋霜” 都是自带高洁感的意象,可 “琨” 字到底读 “kūn” 还是 “hún”?单看字面像在描绘玉石与秋霜的景致,却猜不透为何要将这两种事物组合,更不清楚它的核心指向是写景、咏物还是喻人。今天咱们先把读音校准,再拆解这四字里藏着的纯粹与庄重。 一、“琨玉秋霜”
“琨玉秋霜”怎么读?到底有什么含义?“琨玉秋霜” 中的“玉” 和 “秋霜” 都是自带高洁感的意象,可 “琨” 字到底读 “kūn” 还是 “hún”?单看字面像在描绘玉石与秋霜的景致,却猜不透为何要将这两种事物组合,更不清楚它的核心指向是写景、咏物还是喻人。今天咱们先把读音校准,再拆解这四字里藏着的纯粹与庄重。 一、“琨玉秋霜”
-
 2022高考英语基础知识点!西安伊顿老师带你了解!2022高考英语基础知识点!西安伊顿老师带你了解!高中的英语是一个需要长期积累以及记忆的科目,在高考中只有针对这些知识进行一定的了解和积累,才可以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针对这种情况,小编请到了西安伊顿老师来给大家总结归纳一下关于高考英语基础知识点的记忆内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对于英语还是需要靠日
2022高考英语基础知识点!西安伊顿老师带你了解!2022高考英语基础知识点!西安伊顿老师带你了解!高中的英语是一个需要长期积累以及记忆的科目,在高考中只有针对这些知识进行一定的了解和积累,才可以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针对这种情况,小编请到了西安伊顿老师来给大家总结归纳一下关于高考英语基础知识点的记忆内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对于英语还是需要靠日 -
 关于“呐喊与行动那个更重要”的辩论稿写作指导!一直以来,辩论稿的写作都是大家司空见惯的,但是也是很多同学容易忽视的。现在的语文作文考察的范围和广度越来越大,涉及到的文体也越来越多,因此大家在备考语文作文的时候,还是要增加自己的知识面,增加自己的见识。辩论稿大家见得比较多,但是在语言文字上以及结构上的学习,还是非常值得探究的,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了一则辩论稿,大家可以练习一下。
关于“呐喊与行动那个更重要”的辩论稿写作指导!一直以来,辩论稿的写作都是大家司空见惯的,但是也是很多同学容易忽视的。现在的语文作文考察的范围和广度越来越大,涉及到的文体也越来越多,因此大家在备考语文作文的时候,还是要增加自己的知识面,增加自己的见识。辩论稿大家见得比较多,但是在语言文字上以及结构上的学习,还是非常值得探究的,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了一则辩论稿,大家可以练习一下。 -
 “直播带货”有关的作文写作指导!立意和审题指导!高中的作文写作更多的是来自于社会现象的思考,或者生活的思考,所以高中的同学在写作文的时候可以从生活细节入手,寻找素材,因为任何题目都是取之于生活,进而引发的一系列的思考行为。本次伊顿教育小编给大家分享的这篇作文也是一个社会现象的评述,材料内容是关于“直播带货”,这个大家都是不陌生的,而且有的同学也是参与者,所以对于此也是非常的熟悉的。下面我们可以来看看这篇作文写作的指导。
“直播带货”有关的作文写作指导!立意和审题指导!高中的作文写作更多的是来自于社会现象的思考,或者生活的思考,所以高中的同学在写作文的时候可以从生活细节入手,寻找素材,因为任何题目都是取之于生活,进而引发的一系列的思考行为。本次伊顿教育小编给大家分享的这篇作文也是一个社会现象的评述,材料内容是关于“直播带货”,这个大家都是不陌生的,而且有的同学也是参与者,所以对于此也是非常的熟悉的。下面我们可以来看看这篇作文写作的指导。 -
 2021年9月山水联盟高三开学联考数学试卷及答案(原版)!2021年9月山水联盟高三开学联考已经结束,伊顿教育小编给大家整理了本次联考的数学试卷以及答案,各位相关的小伙伴可以参考一下。对于高三的学习,小编建议大家在每一次的考试之后,都能够仔细的分析一下自己的失分点,对于自己没有掌握的知识点可以尽早的掌握。
2021年9月山水联盟高三开学联考数学试卷及答案(原版)!2021年9月山水联盟高三开学联考已经结束,伊顿教育小编给大家整理了本次联考的数学试卷以及答案,各位相关的小伙伴可以参考一下。对于高三的学习,小编建议大家在每一次的考试之后,都能够仔细的分析一下自己的失分点,对于自己没有掌握的知识点可以尽早的掌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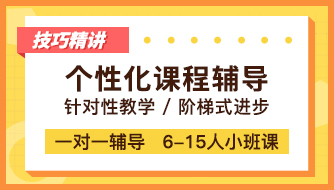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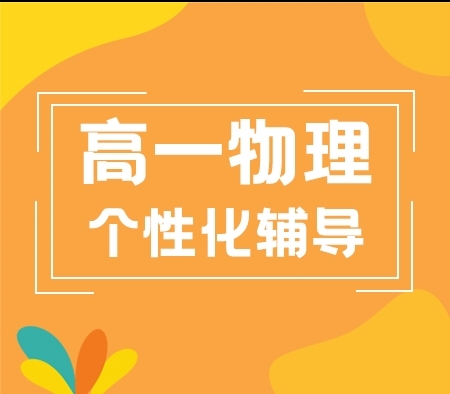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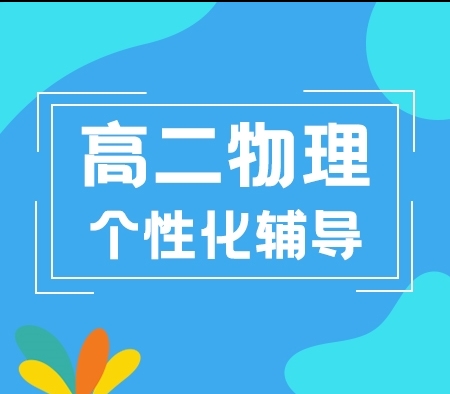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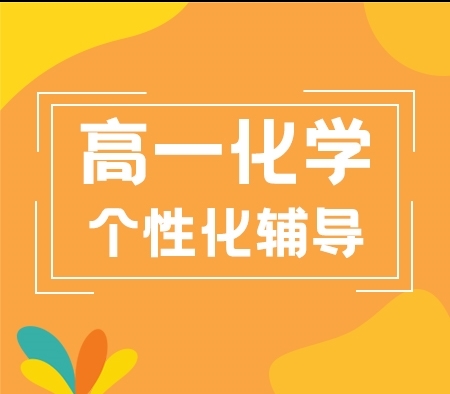





 All right reserved
All right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