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景抒情作文 《路——延展的岁月》 抒情散文分享
文人墨客,唤我阡陌;布衣耕者,呼我街巷。我名山路,泥石作身,尘沙着衣。我,延展向彼方,延展出岁月,更延展向希望。

八十年代的日色,总很慢很慢。汉霄苍茫,懒洋洋的日光呢喃软语,烂漫满地金黄,婀娜生曳。我闲望潇湘平楚,轻听芳草饮露,静赏千秋万古浮萍曲故,不觉中心生困倦。惊鸿疏影间,兀然违和的抽泣惊醒了我。讶然循声望去,草色残光烟照里,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水眸氤氲失神,眸稍泪痣,彷若潋滟浮光,颓言喃语间,黯黯渗出自弃与怅然。这是个年少感伤情郁于中的孩子吗?我不知道。我看见他身旁的妇人柔声抚慰,也看见他粗暴地吼断妇人温言相劝。依然片语化开天际。“我这种资质平庸,出身僻壤的山里孩子,也就是种一辈子地的命了!”他嗤鼻不屑,“又何谈什么将来,什么梦想呢?”少年冷笑,紧攥着刻遍红痕的试卷的手却青筋凸显。是倔强,是不甘,半晌,却又无力地松散。妇人有许心疼,夹杂无奈,敛眉良久,引他眺望我的尽头。“它的尽头是什么?”她没有去看少年眼中的不解,顾自侃侃。“它没有钢筋铁骨,也不出身风光如画的水乡,只是我们踏出的土路,可你又能道明它延展向哪里吗?”她微顿,望着少年欲辩却无言。“它延展向未知的彼方,更延展向无尽的希望。”她眸光空明,映着俱净风烟,鸢飞戾天;也映着少年拭泪微颔,神色愈坚。暮霭斜曛,染迢迢纤云,泛散霞光四散。我笑了,心生柔软,原来这般粗俗的我,也能给他人带去莫大的希望,真好。
九十年代的月影,总很软很软。竹林晚风,弱柳水寒,月色如水水如天,流岚冷冷渐翩跹。尘缘飞花,风华流砂,打眼一过便十载春冬秋夏。我可以说是永生。常人所道海枯石烂旷日经年,于我不过花落花开云舒云卷。听月渐离,不复曾经那般的震慑了,微叹,已历尽千帆,又何谈惊艳?极目远方,却眺望见一对父子般的身影。父亲是个正装革履的青年,小有作为的模样。我轻怔,小镇上有这号人物吗?那竟颇熟识的眉宇英气间,泛着些许初为人父的青涩,小心翼翼地牵着个周岁大的孩童蹒跚着。月影婆娑,镂空他悠远的声音。“知道吗?无论脚下的路,几多僻远,几多蹇劣,它都能延展向很远很远的彼方,延展出极多极多的希望。”他眸光若水般温柔,满映着孩童稚嫩的面容。“昔时那年,我也是踏着它,走向希望。以后,也要让更多的孩子,踏着这条路,走向希望啊!”他的话,孩童听不懂,只望着父亲咿呀笑着,却唤开我记忆的闸门,青年眉眼弯弯,眸稍泪痣,似经久前清晰可辨。数帧流光剪影纷落九尘,喷薄交织与他肖貌相重。沧海横流下,光年流转间,原来那个曾泣下沾巾的少年也拥有了希望,将传递希望啊!我笑了,心生温暖,原来这般拙陋的我,也能给更多的人带去希望,真好。
曾记否,几何时,日色月影下的帧帧画影,悸动了我心,也悸动了无数山里孩子们的心。更多的孔子,踏上我,走向未知的彼方,走出岁月,更走向希望。
- 热门课程
- 热门资讯
- 热门资料
- 热门福利
-
 黄河小班课人数多吗?教学效果怎么样?黄河小班课之前就有家长和学生想要了解过,今天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小编就来好好给大家解答一下关于黄河小班课的一些内容,让大家能够更加方便地做出选择。 一、黄河小班课人数多吗? 黄河小班课的人数控制得挺讲究,既不是那种三五个人的微型小组,也不会像其他学校那样挤着四五十个人,一个班大概在6到15人
黄河小班课人数多吗?教学效果怎么样?黄河小班课之前就有家长和学生想要了解过,今天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小编就来好好给大家解答一下关于黄河小班课的一些内容,让大家能够更加方便地做出选择。 一、黄河小班课人数多吗? 黄河小班课的人数控制得挺讲究,既不是那种三五个人的微型小组,也不会像其他学校那样挤着四五十个人,一个班大概在6到15人 -
 “白驹过隙”怎么读?到底有什么含义?“白驹过隙” 是形容时光的经典表达,可你真能笃定 “驹” 字读 “jū” 而非 “jú”?而且 “白驹” 为何是 “白色的小马”,“过隙” 又特指什么缝隙? 一、“白驹过隙”怎么读? “白驹过隙”的正确读音是bái jū guò xì,“白驹”指白色的骏马,常被引申为太阳的光芒或飞速流逝的时
“白驹过隙”怎么读?到底有什么含义?“白驹过隙” 是形容时光的经典表达,可你真能笃定 “驹” 字读 “jū” 而非 “jú”?而且 “白驹” 为何是 “白色的小马”,“过隙” 又特指什么缝隙? 一、“白驹过隙”怎么读? “白驹过隙”的正确读音是bái jū guò xì,“白驹”指白色的骏马,常被引申为太阳的光芒或飞速流逝的时 -
 博大单招在文化课提升方面优势如何?补习效果好吗?单招相信第一次接触的家长和同学们有很多问题都不了解,很多家长为了让孩子更好地学习就去选择一个合适的单招补习,那么博大单招在这方面的优势到底怎么样?能不能帮助孩子更好地提升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好好了解一下。 一、博大单招在文化课提升方面优势如何? 博大单招在文化课提升这方面那真的是研究得透透的
博大单招在文化课提升方面优势如何?补习效果好吗?单招相信第一次接触的家长和同学们有很多问题都不了解,很多家长为了让孩子更好地学习就去选择一个合适的单招补习,那么博大单招在这方面的优势到底怎么样?能不能帮助孩子更好地提升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好好了解一下。 一、博大单招在文化课提升方面优势如何? 博大单招在文化课提升这方面那真的是研究得透透的 -
 “琨玉秋霜”怎么读?到底有什么含义?“琨玉秋霜” 中的“玉” 和 “秋霜” 都是自带高洁感的意象,可 “琨” 字到底读 “kūn” 还是 “hún”?单看字面像在描绘玉石与秋霜的景致,却猜不透为何要将这两种事物组合,更不清楚它的核心指向是写景、咏物还是喻人。今天咱们先把读音校准,再拆解这四字里藏着的纯粹与庄重。 一、“琨玉秋霜”
“琨玉秋霜”怎么读?到底有什么含义?“琨玉秋霜” 中的“玉” 和 “秋霜” 都是自带高洁感的意象,可 “琨” 字到底读 “kūn” 还是 “hún”?单看字面像在描绘玉石与秋霜的景致,却猜不透为何要将这两种事物组合,更不清楚它的核心指向是写景、咏物还是喻人。今天咱们先把读音校准,再拆解这四字里藏着的纯粹与庄重。 一、“琨玉秋霜”
-
 2022高考英语基础知识点!西安伊顿老师带你了解!2022高考英语基础知识点!西安伊顿老师带你了解!高中的英语是一个需要长期积累以及记忆的科目,在高考中只有针对这些知识进行一定的了解和积累,才可以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针对这种情况,小编请到了西安伊顿老师来给大家总结归纳一下关于高考英语基础知识点的记忆内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对于英语还是需要靠日
2022高考英语基础知识点!西安伊顿老师带你了解!2022高考英语基础知识点!西安伊顿老师带你了解!高中的英语是一个需要长期积累以及记忆的科目,在高考中只有针对这些知识进行一定的了解和积累,才可以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针对这种情况,小编请到了西安伊顿老师来给大家总结归纳一下关于高考英语基础知识点的记忆内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对于英语还是需要靠日 -
 关于“呐喊与行动那个更重要”的辩论稿写作指导!一直以来,辩论稿的写作都是大家司空见惯的,但是也是很多同学容易忽视的。现在的语文作文考察的范围和广度越来越大,涉及到的文体也越来越多,因此大家在备考语文作文的时候,还是要增加自己的知识面,增加自己的见识。辩论稿大家见得比较多,但是在语言文字上以及结构上的学习,还是非常值得探究的,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了一则辩论稿,大家可以练习一下。
关于“呐喊与行动那个更重要”的辩论稿写作指导!一直以来,辩论稿的写作都是大家司空见惯的,但是也是很多同学容易忽视的。现在的语文作文考察的范围和广度越来越大,涉及到的文体也越来越多,因此大家在备考语文作文的时候,还是要增加自己的知识面,增加自己的见识。辩论稿大家见得比较多,但是在语言文字上以及结构上的学习,还是非常值得探究的,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了一则辩论稿,大家可以练习一下。 -
 “直播带货”有关的作文写作指导!立意和审题指导!高中的作文写作更多的是来自于社会现象的思考,或者生活的思考,所以高中的同学在写作文的时候可以从生活细节入手,寻找素材,因为任何题目都是取之于生活,进而引发的一系列的思考行为。本次伊顿教育小编给大家分享的这篇作文也是一个社会现象的评述,材料内容是关于“直播带货”,这个大家都是不陌生的,而且有的同学也是参与者,所以对于此也是非常的熟悉的。下面我们可以来看看这篇作文写作的指导。
“直播带货”有关的作文写作指导!立意和审题指导!高中的作文写作更多的是来自于社会现象的思考,或者生活的思考,所以高中的同学在写作文的时候可以从生活细节入手,寻找素材,因为任何题目都是取之于生活,进而引发的一系列的思考行为。本次伊顿教育小编给大家分享的这篇作文也是一个社会现象的评述,材料内容是关于“直播带货”,这个大家都是不陌生的,而且有的同学也是参与者,所以对于此也是非常的熟悉的。下面我们可以来看看这篇作文写作的指导。 -
 2021年9月山水联盟高三开学联考数学试卷及答案(原版)!2021年9月山水联盟高三开学联考已经结束,伊顿教育小编给大家整理了本次联考的数学试卷以及答案,各位相关的小伙伴可以参考一下。对于高三的学习,小编建议大家在每一次的考试之后,都能够仔细的分析一下自己的失分点,对于自己没有掌握的知识点可以尽早的掌握。
2021年9月山水联盟高三开学联考数学试卷及答案(原版)!2021年9月山水联盟高三开学联考已经结束,伊顿教育小编给大家整理了本次联考的数学试卷以及答案,各位相关的小伙伴可以参考一下。对于高三的学习,小编建议大家在每一次的考试之后,都能够仔细的分析一下自己的失分点,对于自己没有掌握的知识点可以尽早的掌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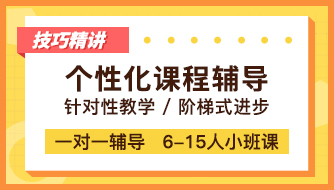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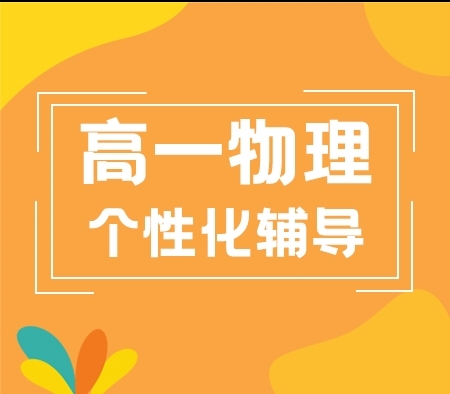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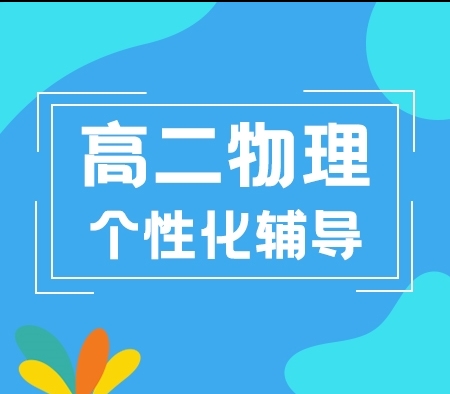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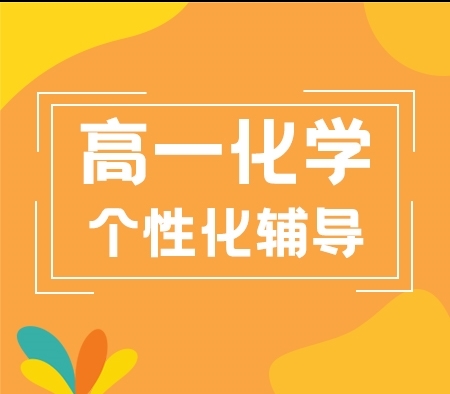





 All right reserved
All right reserved
